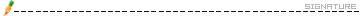新石器时代晚期/良渚文化/玉琮 (Ca.3300~2200 B.C.)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,玉琮是一种非常重要礼器。它的基本造形为方柱体,内有贯穿的大圆孔。方形,反映出古代中国人「地方」的宇宙观;而贯通的圆洞,可能是象征生民与神祇世界间的「沟通」。 华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琮上,则常琢有特殊的「面纹」,代表着神祇、祖先及神灵动物。「面纹」的表现方式有繁有简。本院所藏的这件琮,外壁共分十七节,每一节以四个近90度转角的边棱为「面纹」的中轴,向左右两侧各铺展最简化的「面纹」─以两道饰有平行弦纹的长横棱表示「冠」,一道短横棱表示「鼻子」,两个浅圆圈表示「眼睛」,但因年代久远,表示眼睛的小圆圈已模糊不清。 最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件琮上,直槽的顶端均隐藏着一个图像。从表现方式可知,这个图像并不是为了装饰,因为它的线条又浅又细,并且断断续续,如果不仔细观看,是不易察觉的,因此我们推测,此图像可能是一种「密码」,人与神沟通的密码。由于年代久远,四个中的两个已漫漶不清。
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前期/玉鹰纹圭 (Ca.2500~1600B.C.) 这件玉「圭」是一个由工具、武器的型态,转化为礼制用器的例子。器呈窄长方形,有平直刀刃,原本为铲的形式。但在器身中段的两面,均琢碾了精致的纹饰。一面的上节浮雕向上冲飞的鹰鸟,表现了威猛的神力。而另面则浮雕一抽象的面纹,正中央为高耸的「介」字形冠顶,而两侧插有华丽蓬松的凤羽,线条极为流畅。由许多文献可知,鸟是东夷族群的重要宗教象征:上古时期,华东地区的夷人,相信其始祖为自然界诸神的主宰「帝」所生,而「玄鸟」则是引渡生命力的使者、媒介,即所谓「鸟生神话」。此件玉圭上,出现写实的鹰纹及抽象的凤鸟纹,似乎批露了某些重要而值得探索的讯息。另外,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:在圭的一个侧面,约1平方公分的面积上,琢有一侧面人首,戴船形帽、留卷翘的长发,眼耳鼻口等细节无一省略,非常精致。 器身的上下段,则在清乾隆皇帝时加琢御制诗和玺文。有趣的是,后加的文字与原有的纹饰走向颠倒,因而常常引起观赏者的误解。
汉/玉角形杯 (206B.C.~A.D.220) 玉杯的质地为青白色的闪玉,杂有褐色斑。杯身似兽角,而横断面则呈圆角的长方形。器的正面饰一龙纹,从左上方起首,躯体呈s形向下延伸至器底,接着尾部大幅度扭转到器的背面后再向上攀升,约在杯身的三分之二处回向,继而沿杯外侧的弧度徐缓下降,于杯的右下方盘卷成一圆后终结。首、身、尾采取不同的表现方式,首、尾为高浮雕,身则为浅浮雕。器的背面浅浮雕一凤鸟,身躯亦呈S形。超过比例的长尾一直延续至杯底与龙尾相接,而顶部的凤冠也出乎意料的高耸华丽。纹饰的处理虚实相间,布局四方呼应,具有律动感,且十分平衡和谐。 考古数据中,取兽角为器形者,数量不在少数,其质地包括陶、铜及玉,而时代则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汉、唐。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一件西汉的玉角形杯,形式与本器接近。若从技艺的角度评比,则院藏的玉杯所呈现的技巧较为成熟老练,但也较为制式化。依此推测,本件玉杯的年代略晚于南越王墓出土者。 院藏的玉杯附一精致的紫檀木座。木座外壁缕雕成层层起伏汹涌的波涛,波涛中一面有背载着「河图」的龙马;一面则驮负着「洛书」的灵龟。座内阴刻泥金「商山吴俟侯式」六字,尚不明其意
宋/真宗/禅地玉册及玉嵌片 简长:29.5~29.8cm 简宽:2cm 「封禅」,在中国政治制度中,可说是最盛大,但也争议最多的一项典礼。所谓「封」就是天子登上泰山筑坛祭天;而「禅」则是在泰山下的小丘除地祭地,向天地宣告人间太平。民初疑古派的史家认为,这纯粹是战国至秦汉间,齐儒凭空杜撰,并为好大喜功的君主利用来巩固政权、夸侈政绩的活动。但从近年考古资料看来,其起源或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先民筑坛祭祀的习俗,是非常幽远的。 「封禅」最令人质疑的,还是祭典中的祝祷文,在唐玄宗以前的历代史书内,均未见记载。唐代名臣贺之章将此现象解释为,封禅帝王所求不外为长生登仙等私欲,故外人莫知之。民国二十年,马鸿逵将军率领军队驻扎于山东泰安,无意间发现一座五色土坛,并从其中得到两套玉册。玉册上分别镌刻着唐玄宗及宋真宗禅地之祝祷文。两套玉册的出土,正可以补足刊正史籍的阙如与错植,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史料。 宋真宗禅地玉册的质地为青白色闪玉。册分十六简,简与简间以金线串联。册文以楷体书写后刻划,并涂以金漆,与唐册相比,字迹显得松散。近日发现,其中两简的背面有磨去原刻字的情形,根据残余笔划推测,似乎是宋太祖、太宗谥号的部份。对照《宋史》发现,二帝的谥号在册与史的记载中确有繁简之别,而修改的原因,可能是因为在禅地前的两个月,才为二先帝新进谥号的缘故。
除了玉册,还有一些正方、长方或梯形的玉片共五十二件同时出土。这些玉片上主要装饰着龙、凤及云气纹。根据史书记载,盛装玉册的容器是所谓玉匮,推测这些玉片便是玉匮上的组件
宋─明/玉荷叶杯 长15.2cm 宽5.9cm 高9cm 除底部微微露出玉质原有的黄绿色外,通体褐黄,部份显现灰白斑,偶见褐红的色素,掺杂于阴刻线中。状如枯槁而包阖起的荷叶,呈上宽下敛的三角形。叶缘弯曲起皱。外壁双阴刻线刻划叶脉。叶梗在底部弯绕一圈后顺势上扬至杯侧,此一安排除了增添造形的变化外,还具有器足与器把的实际功能。而此设计与浙江衢洲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一只白玉荷叶杯相似,只是本器的手法更见成熟。本器的附件紫檀木座,以多层次镂雕作一把莲状,花叶秀美清雅,益添玉杯之风采, 文豪苏东坡曾谓晨饮为「浇书」,婉转而幽默的表达出知识分子不得志时,惆怅但又不放弃理想、希望的心态。或许是心有戚戚,明代的陈洪绶遂在其「画隐居十六观册」中安排了「晨饮」这个主题。图中东坡先生坐在木根椅中,手持的正是一只与此件展品相似的荷叶杯。在此,荷叶杯具有文人不向恶劣环境屈服的象征意义。明代的陈洪绶遂在其「画隐居十六观册」〈现藏本院〉中安排了「晨饮」这个主题。图中东坡先生坐在木根椅中,手持的正是一只与此件展品相似的荷叶杯。
元─明/大雁玉带饰 长11.2cm 宽6.2cm 器近椭圆形。白玉质,光泽温润莹秀。正面采多层次镂空技法,呈现大雁穿窜于荷塘苇丛间的景况。背面,中央有一长方形框,面上浅\\\浮雕如意云纹,框的两侧嵌有铜质带扣,以供穿系革带之用。 此件玉带饰的纹样与鲜卑、女真族的生活习俗有关。据辽、金史书的记载,每年春季,皇帝均率臣子至河岸以「海东青」猎雁鹅,所谓「春捺」,远泊鸣鼓,鹅惊腾起,...五坊擎进海东青鹘,拜授皇帝放之,鹘擒鹅坠...」。海东青,鹰的一种,主要产于女真人的故乡─黑龙江流域,体型甚小但擅捕雁、鹅等大形的鸟类,常迫之窜躲于荷叶、芦苇之中。辽、金的服饰,常见以鹰擒鹅坠的剎那为装饰纹样。﹝金史‧舆服志﹞中载,「其从春水之服,多鹘捕鹅杂花卉饰」,故而这类纹饰题材我们称之为「春水」。 元代仍可见以「春水」为题材的服饰。而到明代,因为民族的差异性,「春水」中游牧民族的狩猎特质淡化,所以常常有仅见雁而不见鹰的情形。这件玉饰还保留着元朝带饰的椭圆造型,而风格上也比较接近元代:层次杂而不乱、线条圆鼓而滑顺,只是仅留大雁在荷莲中穿行,而不见鹘鹰巡狩的画面,使我们估量,它或许是制作于一个交替过渡的时期。
清/翠玉白菜 长18.7cm 高9.1cm 厚:5.07cm 玉,在中国是非常珍贵的质材,琢磨玉料成为器物则相当的费工、费时,如何节料、省工遂成为玉器设计过程中,空间思考的准则之一,而「量材就质」便是此思考方向下产生的艺术特质。所谓「量材就质」,简而言之,就是顺应玉料自然天成的外形或色泽设计玉器形制,是一种在外设条件的限制下发挥创造力的创作方式。协调天然与人为,则是此一创作方式最重要的理念。本院藏品「翠玉白菜」即可谓其中翘楚-以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材,运用玉料自然的色泽分布,琢碾出一棵鲜活欲滴、叶片上还停留了两只螽斯的白菜。 此件翡翠玉白菜原是永和宫的陈设器,永和宫为清末瑾妃所居之宫殿,据说翠玉白菜即为其随嫁的嫁妆。白菜寓意清白;象征新嫁娘的纯洁,螽斯则象征多产;祈愿新妇能子孙众多。自然色泽、人为形制、象征意念,三者搭配和谐,遂成就出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。